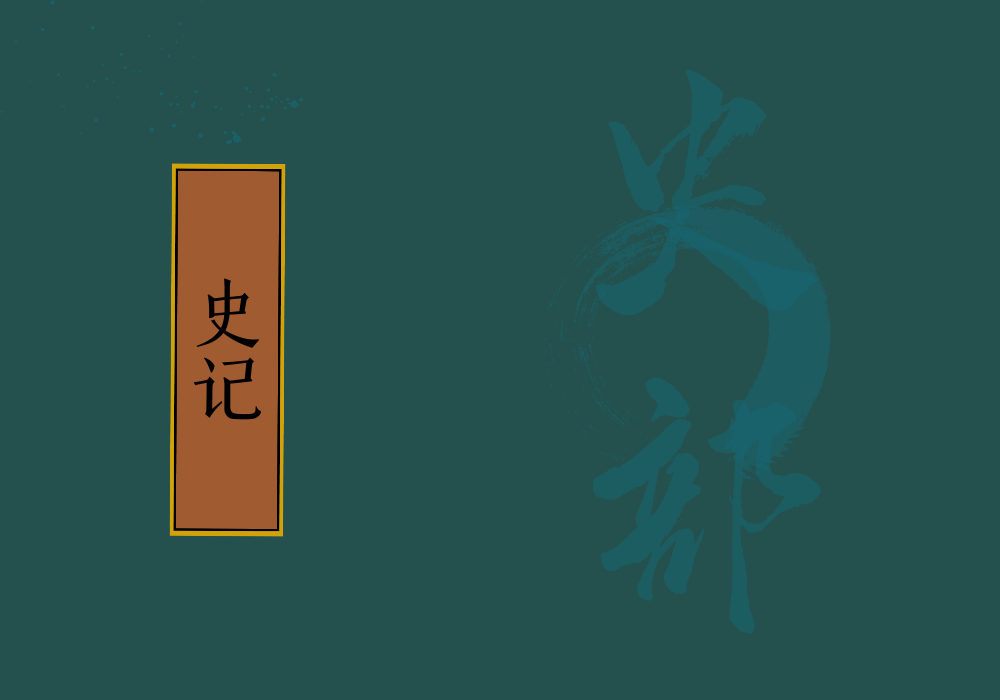自古受命而王【受命而王:禀受天命而成为君主。】,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!其于周尤甚,及秦可见。代王之入,任【任:听信。】于卜者。太卜之起,由汉兴而有。
司马季主者,楚人也。卜于长安东市。
宋忠为中大夫,贾谊为博士,同日俱出洗沐【洗沐:汉代时官吏有假期以洗沐,因此洗沐代指休假。】,相从论议,诵易先王圣人之道术,究遍人情,相视而叹。贾谊曰:“吾闻古之圣人,不居朝廷,必在卜医之中。今吾已见三公九卿朝士大夫,皆可知矣。试之卜数中以观采【观采:观看其风采。】。”二人即同舆而之市,游于卜肆中。天新雨,道少人。司马季主闲坐,弟子三四人侍,方辩天地之道,日月之运,阴阳吉凶之本。二大夫再拜谒。司马季主视其状貌,如类有知者,即礼之,使弟子延之坐。坐定,司马季主复理前语,分别【分别:分辨,剖析。】天地之终始,日月星辰之纪,差次仁义之际,列吉凶之符,语数千言,莫不顺理。
宋忠、贾谊瞿然【瞿然:惊恐害怕的样子。瞿,通“惧”,害怕。】而悟,猎缨【猎缨:整理好帽子。猎,此处指用手捋齐,捋正。缨,帽带。】正襟危坐,曰:“吾望先生之状,听先生之辞,小子窃观【窃观:私下观察。】于世,未尝见也。今何居之卑【居之卑:处于低下地位。卑:卑下。】,何行之污【行之污:从事的职业被人瞧不起。行,行事,此处指从事的职业。污,污浊、不干净。】?”
司马季主捧腹大笑曰:“观大夫类有道术者,今何言之陋也,何辞之野【野:粗鄙。】也!今夫子所贤者何也?所高者谁也?今何以卑污长者【长者:司马季主自指。】?”
二君曰:“尊官厚禄,世之所高也,贤才处之。今所处非其地,故谓之卑。言不信,行不验,取不当【取不当:用不正当手段谋取。】,故谓之污。夫卜筮者,世俗之所贱简也。世皆言曰:‘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,虚高人禄命以说人志,擅言祸灾以伤人心,矫【矫:捏造。】言鬼神以尽人财,厚求拜谢以私于己。’此吾之所耻,故谓之卑污也。”
司马季主曰:“公且安坐。公见夫被发童子乎?日月照之则行,不照则止,问之日月疵瑕【日月疵瑕:指日食和月食。疵瑕,即瑕疵,小的毛病、缺点。古人常借观察星象来推测人事的吉凶。】吉凶,则不能理【理:整理。此处意为解释说明,讲出道理。】。由是观之,能知别【知别:识别。】贤与不肖者寡矣。
“贤之行也,直道以正谏,三谏不听则退【退:辞官。】。其誉【誉:称赞。】人也不望其报,恶【恶:批评责备。】人也不顾其怨,以便国家利众为务。故官非其任不处也,禄非其功不受也;见人不正,虽贵不敬也;见人有污,虽尊不下也;得不为喜,去不为恨;非其罪也,虽累辱而不愧也。
“今公所谓贤者,皆可为羞矣。卑疵【卑疵:卑躬屈膝的样子。】而前,孅趋【孅趋:过分谦恭。】而言;相引以势,相导以利;比周【比周:与小人亲近,结党营私。】宾正【宾正:排挤正直的人。宾,通“摈”。】,以求尊誉,以受公奉;事私利,枉主法,猎农民;以官为威,以法为机,求利逆暴:譬无异于操白刃劫人者也。初试官时,倍力为巧诈,饰虚功执空文以罔主上,用居上为右;试官不让贤陈功,见伪增实,以无为有,以少为多,以求便势尊位;食饮驱驰,从姬歌儿,不顾于亲,犯法害民,虚公家:此夫为盗不操矛弧者也,攻而不用弦刃者也,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。何以为高贤才乎?
“盗贼发不能禁,夷貊【夷貊:泛指少数民族。】不服不能摄【摄:同“慑”,震慑。】,奸邪起不能塞【塞:制止。】,官耗乱不能治,四时不和不能调,岁谷不孰【孰:通“熟”,成熟,丰收。】不能适。才贤不为,是不忠也;才不贤而托官位,利上奉,妨贤者处,是窃位也;有人者进,有财者礼,是伪也。子独不见鸱枭【鸱枭:本意指猫头鹰,这里用来指代奸邪小人。】之与凤皇翔乎?兰芷芎<生僻字>【兰芷芎<生僻字>:指各种香草。】弃于广野,蒿萧【蒿萧:指各种臭草。】成林,使君子退而不显众,公等是也。
“述而不作【述而不作:转述前人旧闻而没有开创自己的新说。】,君子义也。今夫卜者,必法天地,象四时,顺于仁义,分策定卦,旋式正棋,然后言天地之利害,事之成败。昔先王之定国家,必先龟策日月,而后乃敢代;正时日,乃后入家;产子必先占吉凶,后乃有之。自伏羲作八卦,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。越王句践放文王八卦以破敌国,霸天下。由是言之,卜筮有何负哉!
“且夫卜筮者,埽除设坐,正其冠带,然后乃言事,此有礼也。言而鬼神或以飨,忠臣以事其上,孝子以养其亲,慈父以畜其子,此有德者也。而以义【以义:按照实际情况。】置数十百钱,病者或以愈,且死或以生,患或以免,事或以成,嫁子【嫁子:嫁女儿。】娶妇或以养生:此之为德,岂直数十百钱哉!此夫【此夫:这就是。】老子所谓‘上德不德,是以有德’。今夫卜筮者利大【利大:贡献大。】而谢少【谢少:索取少。】,老子之云岂异于是乎?
“庄子曰:‘君子内无饥寒之患,外无劫夺之忧,居上而敬,居下不为害,君子之道也。’今夫卜筮者之为业也,积之无委聚,藏之不用府库,徙之不用辎车,负装之不重,止而用之无尽索【索:穷尽。】之时。持不尽索之物,游于无穷之世,虽庄氏之行未能增于是也,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?天不足西北,星辰西北移;地不足东南,以海为池;日中必移,月满必亏;先王之道,乍存乍亡。公责卜者言必信,不亦惑乎!
“公见夫谈士辩人乎?虑事定计,必是人也,然不能以一言说人主意,故言必称先王,语必道上古;虑事定计,饰先王之成功,语其败害,以恐喜人主之志,以求其欲。多言夸严,莫大于此矣。然欲强国成功,尽忠于上,非此不立。今夫卜者,导惑教愚也。夫愚惑之人,岂能以一言而知之哉!言不厌多。
“故骐骥【骐骥:千里马。】不能与罢驴【罢驴:疲惫的驴子,指劣等驴。罢,同“疲”。】为驷,而凤皇不与燕雀为群,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。故君子处卑隐以辟众,自匿以辟伦,微见德顺以除群害,以明天性,助上养下,多其功利,不求尊誉。公之等喁喁【喁喁:众人仰慕的样子。】者也,何知长者之道乎!”
宋忠、贾谊忽而自失,芒乎无色,怅然噤口不能言。于是摄衣而起,再拜而辞。行洋洋也,出门仅能自上车,伏轼低头,卒不能出气。
居三日,宋忠见贾谊于殿门外,乃相引屏语【屏语:避开他人私语。】相谓自叹曰:“道高益安,势高益危。居赫赫【赫赫:显赫的样子。】之势,失身且有日矣。夫卜而有不审【审:准确。】,不见夺糈【糈:精米,这里指代财物。】;为人主计而不审,身无所处。此相去远矣,犹天冠地屦【屦:鞋。】也。此老子之所谓‘无名者万物之始’也。天地旷旷,物之熙熙【熙熙:热闹的样子。】,或安或危,莫知居之。我与若,何足预彼哉?彼久而愈安,虽曾氏之义未有以异也。”
久之,宋忠使匈奴,不至而还,抵罪。而贾谊为梁怀王傅,王堕马薨,谊不食,毒恨【毒恨:悔恨。】而死。此务华绝根者也。
太史公曰: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,多不见于篇。及至司马季主,余志而着之。
褚先生曰:臣为郎时,游观长安中,见卜筮之贤大夫,观其起居行步,坐起自动,誓正其衣冠而当乡人也,有君子之风。见性好解妇【性好解妇:性情和顺,体贴人意的女子。】来卜,对之颜色严振【严振:严肃。】,未尝见齿而笑【见齿而笑:笑得露出牙齿,在古时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。见,通“现”。】也。从古以来,贤者避世,有居止【居止:居住。】舞泽者,有居民间闭口不言,有隐居卜筮间以全身者。夫司马季主者,楚贤大夫,游学长安,通《易经》,术黄帝、老子,博闻远见。观其对二大夫贵人之谈言,称引古明王圣人道,固非浅闻小数之能。及卜筮立名声千里者,各往往而在。传曰:“富为上,贵次之;既贵各各学一伎能立其身。”黄直,大夫也;陈君夫,妇人也:以相马立名天下。齐张仲、曲成侯以善击刺学用剑,立名天下。留长孺以相彘立名。荥阳氏以相牛立名。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,皆有高世绝人之风,何可胜言。故曰:“非其地,树之不生;非其意,教之不成。”夫家之教子孙,当视其所以好,好含苟生活之道,因而成之。故曰:“制宅命子【命子:教育孩子。】,足以观士;子有处所,可谓贤人。”
臣为郎时,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【同署:同一个办公单位。】,言曰:“孝武帝时,聚会占家问之,某日可取妇乎?五行家【五行家:研究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间关系的人。】曰可,堪舆家【堪舆家:风水先生。】曰不可,建除家【建除家:以观测天象占卜吉凶的人。】曰不吉,丛辰家【丛辰家:以研究阴阳五行与岁月日时相配而占卜吉凶的人。】曰大凶,历家【历家:推算历象的人。】曰小凶,天人家【天人家:研究天人感应的人。】曰小吉,太一家【太一家:研究术数的道家流派。】曰大吉。辩讼不决,以状闻。制曰:‘避诸死忌,以五行为主。’”人取于五行者也。
译文
从古至今君主都是承受天命而成为帝王的,帝王的兴起又如何不是依靠卜筮的方法由天命决定的呢!这种形式在周朝时最为兴盛,等到秦朝时仍可见到。汉朝时嗣君的选定,都是取决于占卜者。太卜官员的兴起,汉朝兴起就已经出现了。
司马季主,是楚国人。在长安城的东市为人占卜。
宋忠担任中大夫,贾谊担任博士,一天他们一起外出休假,一边走着一边谈论,讨论讲述着先王圣人的治国之道,广泛地探究世道人情,两人相视感叹。贾谊说:“我听说古时的圣人,不是高居于朝廷之上,就一定身处卜筮或医师的行业之中。如今我们已见识过了三公九卿及朝中的那些士大夫,他们的才能和见识都知道了。我们试着去见识一下卜筮者的风采吧。”于是两人乘同一辆车来到市区,在卜肆筮馆中游逛。天刚刚下过雨,路上行人很少。司马季主正在馆中闲坐,有三四个徒弟在边上侍立,正在探讨天地之间的道理,日月运行的规律,阴阳吉凶的源头。宋忠、贾谊这两位大夫向司马季主拜了两拜。司马季主看到他们的外貌模样,很像是有些知识的人,于是回礼,让徒弟迎二人入坐。坐下之后,司马季主重新讲说起刚刚提到的内容,剖析天地间的终止与起源,日月星辰运行包含的规律,顺序排列及仁义的结合,按此讲述吉凶的征兆,说了几千个字,没有不遵循事理的。
宋忠、贾谊非常惊异而有所领悟,整好冠带,端正衣襟,恭谨地坐着,说:“我们观看先生的容貌,聆听先生的言辞,晚辈私下里观察当今世上,还从未曾见到过。如今先生为什么地位如此卑下,为什么从事让人瞧不起的职业呢?”
司马季主捧腹大笑说:“看起来两位大夫很像是有些道术的人,如今为何有这样浅陋的见识,为什么言辞这样粗野呢!究竟什么样的人能让先生们觉得贤能呢?又是什么样的人能让二位觉得高尚呢?现在凭什么觉得我这样的长者是卑下污秽的呢?”
宋忠、贾谊二人说:“拥有尊贵的官职和丰厚的俸禄,世人都会尊重,贤能的人才能享有它们。如今您所处的并非是那样的地位,因此称之为卑下。说话不能使人尽信,做事不符合实际,索取不合情理,因此称之为污秽。占卜者是世俗所贱视的。世人都说:‘那些占卜者多数都用夸大荒诞的言辞来博取人情,假意抬高求卜人的禄命以取悦人们,编造灾祸以忧伤人心,捏造鬼神之言以骗尽人财,贪求贵重的酬谢以为自己求得利益。’这些都是我们觉得耻辱的事情,因此说卜筮是卑下污秽的职业。”
司马季主说:“先生们暂且安坐。先生们看到过那些披散头发的男孩子吗?日月照到他们身上就走路,照不到就停下来,问他们日食月食的情况和人事吉凶,却说不出什么道理来。由此可见,能区分辨别贤与不贤的人没多少。
“贤者言行举止,遵循正直的道义,以正面的道理来劝谏君王,屡劝而不听从就选择辞官引退。他用美言赞誉别人,并不期望得到别人的回报;以行动表示憎恶别人,也并不会顾忌别人的怨恨,将对国家和百姓有利作为己任。因此倘若官职并非自己能够胜任的就不会做,俸禄与自己的功劳不符就不会要;看到一个人心术不正,纵使他身份尊贵也不会尊敬他;看到一个人行为不端,纵使他地位很高也不会屈居其下;得到官位也不因此而感到欢喜,失去官职也不因此而遗憾;倘若并非自己的过错,纵使因受到牵累而受囚禁的侮辱也不会感到愧疚。
“今天先生们所提到的贤者,都是足以让人感到羞愧的人。他们低声下气地求取晋升,过分谦恭地说话;用权势彼此勾结,用私利互相诱导;结党营私,排斥正人君子,以此求得尊宠和名誉,以此享受公家提供的俸禄;谋求私人利益,歪曲君主法令,剥削百姓财产;凭借官位作威作福,利用法令做工具,追逐私利,倒行逆施:这和手里拿着利刃去抢劫别人的人没有差别。最初试用为官的时候,竭力施展巧诈的手法,虚假粉饰个人的功劳,捏造虚假的结果欺骗君王,以此爬上显赫的地位;做官不允许贤者陈述功劳,反而自我夸耀功劳,发现假的就将它添油加醋地说成是真的,把没有当成有,把少当成多,以求得权势高位;恣意享受吃喝玩乐,驱车外出游玩,带着美姬歌女,不管父母亲人,违法犯纪,残害百姓,令公家财产虚耗:这些人本是强盗却从不拿着利矛木弓的人,是攻击别人却从不使用刀箭的人,是虐待欺凌父母却不会被治罪和弑杀国君却不会被征伐的人。你们怎么觉得这些人是高人贤才呢?
“出现了盗贼不能禁止,少数民族不服从却不能威慑,奸邪兴起却难以遏阻,官府损耗却无法整治,四时不和却不能协调,年景不好却难以调济。身怀贤才却不出来做事,这是对君主不忠;没有贤德和才能却占据官位,享受着皇上的俸禄,阻碍有贤能的人晋升,这是窃居官位;有关系的人就能进用做官,有钱财的人才能得到礼遇,这就是虚伪。你们难道没看到过猫头鹰与凤凰一同飞翔吗?兰芷、芎这些香草都被遗弃在旷野,青蒿、艾萧这些野草却茂密如树林一般,让君子引身而退难以在福斯中显露才华,你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。
“传述而不创作,这是君子本来的道义。如今占卜的人,肯定会效法天地,取象四时的变化,合乎仁义的要求,辨别筮策,定下卦象,转动栻盘,摆正筮綦,然后言说天地间的利益与损害,人事的成功与失败。过去先王创建国家,一定要先使用龟甲和蓍草占卜日月,然后才敢替代上天治理百姓;选好了吉日良辰,然后才敢进入都城;生孩子一定要先占卜一下吉凶,然后才敢受孕怀胎。自打伏羲创制八卦,周文王将其演化成了三百八十四爻象后,天下得以大治。越王句践效仿文王演制的八卦为人行事,这才攻灭了敌国,称霸天下。从这些情况来看,占卜有什么需要忧虑的呢!
“并且占卜的人,洒扫庭除,设下座位,整理好自己的帽子和腰带,然后才言说吉凶之类的事情,这是合乎礼制的行为。他们的言词能够使鬼神享受祭品,忠良的臣子因此而服侍自己的君主,孝顺的子女因此而赡养自己的双亲,慈父因此而养育自己的孩子,这些是合乎道德的表现。请求卜卦的人按照实际情况给占卜人几十上百个钱,生病的人有的因此得以痊愈,快死的人有的因此得以生还,祸灾有的因此得以避免,事情有的因此得以成功,嫁女儿娶媳妇有的因此而能够生养:这种功德,难道仅仅值几十上百个小钱吗?这就是老子所提到的‘至高无上的道德就是没有道德一样,这才是有德’。如今那些占卜的人贡献大却索取少,老子说的话难道和这样的状况有什么不一样吗?
“庄子说:‘君子内心没有挨饿和受冻的担忧,外部没有被抢劫掠夺的忧患,居于高位就谦恭谨慎,处于低位也不为害别人,这就是君子的道义。’如今卜筮的人从事的这个职业,积攒的钱财没能成堆,贮藏的物资用不到仓库,迁往异地不用辎车,行装并没有多重,停了下来就能应用,而且从没有穷尽之时。带着无法用尽的东西,在永无止境的世界中遨游,纵使是庄子自身的行为也不一定能比这样更好吧,先生们因为什么缘故而说不能从事占卜呢?上天在西北方有不足,星辰就向西北方移动;大地在东南方有塌陷,就将大海当作水池;太阳升到了正午就一定会向西落,月亮到了圆满之期就必定趋于亏损;先王留存的道术,有时存有时亡。而二位先生要求卜筮者说话一定要真实,这难道不令人感到迷惑不解吗?
“先生们可曾遇到过那些巧言善辩的人吗?商议事情,制定计划,一定会是这些人。但是他们不能凭借着一两句话让君王高兴,所以说话时一定托称先王,说话必定提及上古;思考问题,决定策略,夸赞粉饰先王的功绩,以及解释他们的失败与祸害,以此来让君王的内心恐惧或是欢喜,以期望满足自己的欲望。言辞繁复而夸张,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。但是希望国家变得富强,事业取得成功,对皇上尽职尽忠,如果不这样做是不行的。现在的卜筮者,是解答迷惑、教化愚顽的人。那些身处愚顽迷惑的人,怎么可以凭借一两句话就能让他们变得聪明呢?因此说话不能因反复陈述而产生厌恶之情。
“所以千里马不可以和疲惫的驴驾同一辆车,凤凰不可以和燕雀同在一群,而贤人也不会和不贤的人处于同列。因此君子处身在卑下隐晦之地以避开凡夫俗子,自我隐匿以躲避世俗人伦,背地里察看天地人事及万物的道理以除去各种祸患,来彰显上天的德性,协助君王养育下民,这些人对世人的功绩很多,却并不追求尊宠的美誉。二位先生这样的人都只是会随声附和的人,怎么会知晓长者的道义呢?”
宋忠、贾谊恍惚中若有所失,茫然失色,神情怅然,面无血色,惆怅不已说不出什么。于是整理好衣衫站起身来,拜了两拜,就辞别司马季主。走起路来无精打采,出门后只能自己爬到车上,趴在车栏上,垂着头,就像透不过气来一样。
三天后,宋忠在大殿门外遇到了贾谊,于是拉着他避开众人谈论起来,彼此慨叹说:“道德越高尚就越安全,权势越大就越危险。身处显赫的位子,丧身之日就不远了。占卜虽然有不太灵验的时候,也不可能被人夺去占卜花费的钱财;要是为君主谋划不周密的话,就难有立身之地。这两种情况相比差距太大了,就如同是天冠地屦一样。这就是老子所提到的‘无名是天地万物的源头’啊。天地辽阔无垠,万物热闹和乐,有的安定,有的危难,没有人知晓自己应该身处何方。我和你,有什么资格去评论那些占卜的人呢?他们的时间过得越久就越安乐,即便是曾子(当为庄子)的道义,也和他们没什么不同吧。”
过了很长时间,宋忠被派出使匈奴,还没抵达目的地就回来了,被判了刑。贾谊做了梁怀王的太傅,怀王掉下马来不幸去世,贾谊因愧疚而绝食,含恨去世。这都是些追逐浮华而失去性命根本的人。
太史公说:古时候的占卜者之所以没有被记录下来,是因为他们的事迹很难在文献典籍中见到。等到了司马季主,我记录下他的言行并撰写了出来。
褚先生说:我担任郎官时,在长安城里游历观察,见到过那些从事占卜行业的贤明大夫,我观察这些人的起居、行路,一切行动都由着自己,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和帽子,虽然有些像乡里人,但却颇有君子的风度。遇到那些性情随、体贴人意的妇人前来占卜,他们也脸色严肃,笑不露齿。从古至今,贤良的人逃避世事习俗,有的隐居在荒野大泽中,有的生活在民间却闭口不谈世事,有的藏身于卜筮职业里以保全身家。司马季主,是楚地贤德的大夫,到长安城里游学,通晓《易经》,可以阐释黄帝与老子的道义,学识广博,见识长远。观察他对宋忠和贾谊两位大夫贵人的谈话,引用古时明王圣人的道理,原本就不是知识浅薄能力低下之辈。倒是那些凭借卜筮安身立命而且扬名千里之外的人,往往无处不在。古书中说:“富足位于上等,尊贵次之;等到身居显贵位置之后,还仍要学会一技之长使自己能够在社会上安身立命。”黄直,是位大夫;陈君夫,是名女子,二人都凭借擅长相马扬名天下。齐地的张仲和曲成侯依靠善于用剑击刺而名扬天下。留长儒凭借相猪立名。荥阳的褚氏依靠相牛而出名。能够凭借技能扬名的人很多,都有高于世俗、超出常人的风采,怎么能说得完呢。因此说:“如果不是合适的地方,无论种什么也不会生长;如果不是自己的意向,无论怎么教导他也无法成功。”家庭教导子孙,应该明察他所喜爱的事物,倘若这种喜好能够包含生存之道,就应该顺势教育并促使他成功。因此说:“管理家庭,教育子女,足以看出士人的为人;子女有了能够安身处世的职业,父亲就能够称得上是贤人。”
我做郎官时,曾经与太卜官待诏为郎的人在同一个衙署做事,他们说:“孝武帝在位时,曾召集了卜筮的各类专家前来问事,某天能够娶媳妇吗?五行家认为可以,堪舆家觉得不行,建除家认为不吉利,丛辰家觉得大凶,历家认为小凶,天人家觉得小吉,太一家认为大吉。各类专家争论不休,难以定论,只好将这种情况报告皇上。皇帝制命说:‘避开那些死凶的忌讳,应该以五行家为主。’”于是人们就采取了五行家的意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