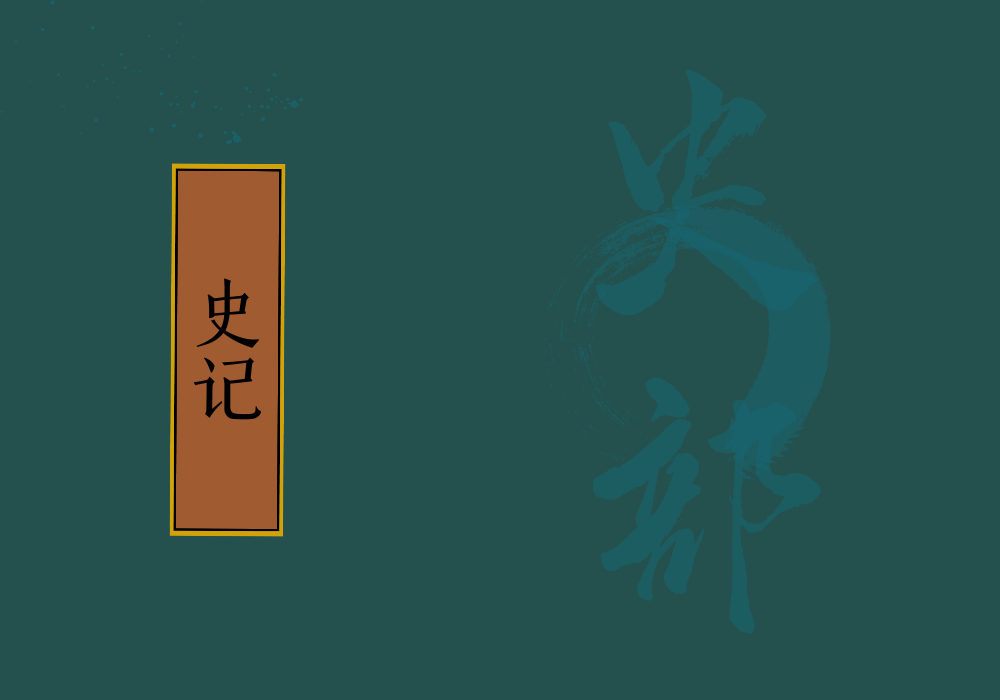万石君名奋,其父赵人也,姓石氏。赵亡,徙居温。高祖东击项籍,过河内,时奋年十五,为小吏,侍高祖。高祖与语,爱其恭敬,问曰:“若【若:你。】何有?”对曰:“奋独有母,不幸失明。家贫。有姊,能鼓琴。”高祖曰:“若能从我乎?”曰:“愿尽力。”于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,以奋为中涓,受书谒【谒:拜见,谒见。】,徙其家长安中戚里,以姊为美人故也。其官至孝文时,积功劳至大中大夫。无文学【文学:指儒术,当时人称通六经礼乐的人为“文学之士”。】,恭谨无与比。
文帝时,东阳侯张相如为太子太傅,免。选可为傅者,皆推奋,奋为太子太傅。及孝景即位,以为九卿;迫近,惮【惮:嫌忌。】之,徙奋为诸侯相。奋长子建,次子甲,次子乙,次子庆,皆以驯行孝谨【驯行:对父母百依百顺。驯,通“顺”。孝谨,孝顺并且谨慎。】,官皆至二千石。于是景帝曰:“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,人臣尊宠乃集其门。”号奋为万石君。
孝景帝季年,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,以岁时为朝臣。过宫门阙,万石君必下车趋,见路马【路马:天子之马,指皇上的车驾。】必式【式:通“轼”。】焉。子孙为小吏,来归谒,万石君必朝服见之,不名。子孙有过失,不谯让【谯让:申斥,责备。】,为便坐,对案不食。然后诸子相责,因长老肉袒固谢罪,改之,乃许。子孙胜冠者在侧,虽燕居必冠,申申如也。僮仆䜣䜣【䜣䜣:恭敬祥和。】如也,唯谨。上时赐食于家,必稽首俯伏而食之,如在上前。其执丧,哀戚甚悼。子孙遵教,亦如之。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,虽齐鲁诸儒质行,皆自以为不及也。
建元二年,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。皇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,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,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,少子庆为内史。
建老白首,万石君尚无恙。建为郎中令,每五日洗沐归谒亲,入子舍,窃问侍者,取亲中裙厕牏【厕牏:便器。】,身自浣涤【浣涤:洗涤,洗净。】,复与侍者,不敢令万石君知,以为常。建为郎中令,事有可言,屏人恣言,极切;至廷见,如不能言者。是以上乃亲尊礼之。
万石君徙居陵里。内史庆醉归,入外门不下车。万石君闻之,不食。庆恐,肉袒请罪,不许。举宗及兄建肉袒【肉袒:脱掉上衣,常用来表示请罪投降。】,万石君让曰:“内史贵人,入闾里【闾里:乡里,泛指民间。】,里中长老皆走匿,而内史坐车中自如,固当!”乃谢罢庆。庆及诸子弟入里门,趋至家。
万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。长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,扶杖乃能行。岁余,建亦死。诸子孙咸孝,然建最甚,甚于万石君。
建为郎中令,书奏事,事下,建读之,曰:“误书!‘马’者与尾当五,今乃四,不足一。上谴死矣!”甚惶恐。其为谨慎,虽他皆如是。
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,御出【御出:为皇帝赶车出行。御,通“驭”。】,上问车中几马,庆以策数马毕,举手曰:“六马。”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,然犹如此。为齐相,举齐国皆慕其家行,不言而齐国大治,为立石相祠。
元狩元年,上立太子,选群臣可为傅者,庆自沛守为太子太傅,七岁迁为御史大夫。
元鼎五年秋,丞相有罪,罢。制诏御史:“万石君先帝尊之,子孙孝,其以御史大夫庆为丞相,封为牧丘侯。”是时汉方南诛两越,东击朝鲜,北逐匈奴,西伐大宛,中国多事。天子巡狩海内,修上古神祠,封禅,兴礼乐。公家用少,桑弘羊等致利,王温舒之属峻法,儿宽等推文学至九卿,更进用事,事不关决于丞相,丞相醇谨【醇谨:淳厚谨慎。】而已。在位九岁,无能有所匡言。尝欲请治上近臣所忠、九卿咸宣罪,不能服,反受其过,赎罪。
元封四年中,关东流民二百万口,无名数【名数:户籍,户口。】者四十万,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适【适:通“谪”,谪罚。】之。上以为丞相老谨,不能与其议,乃赐丞相告归,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。丞相惭不任职,乃上书曰:“庆幸得待罪丞相,罢驽无以辅治,城郭仓库空虚,民多流亡,罪当伏斧质【斧质:也称“斧锧”,古代一种腰斩的刑具。】,上不忍致法。愿归丞相侯印,乞骸骨归,避贤者路。”天子曰:“仓廪既空,民贫流亡,而君欲请徙之,摇荡不安,动危之,而辞位,君欲安归难乎?”以书让【让:责备。】庆,庆甚惭,遂复视事。
庆文深审谨,然无他大略,为百姓言。后三岁余,太初二年中,丞相庆卒,谥为恬侯。庆中子德,庆爱用之,上以德为嗣,代侯。后为太常,坐法当死,赎免为庶人。庆方为丞相,诸子孙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。及庆死后,稍以罪去,孝谨益衰矣。
建陵侯卫绾者,代大陵人也。绾以戏车为郎,事文帝,功次迁为中郎将,醇谨无他。孝景为太子时,召上左右饮,而绾称病不行。文帝且崩时,属【属:通“嘱”,嘱咐。】孝景曰:“绾长者,善遇之。”及文帝崩,景帝立,岁余不噍呵【噍呵:呵斥,训斥。】绾,绾日以谨力。
景帝幸上林,诏中郎将参乘,还而问曰:“君知所以得参乘乎?”绾曰:“臣从车士幸得以功次迁为中郎将,不自知也。”上问曰:“吾为太子时召君,君不肯来,何也?”对曰:“死罪,实病!”上赐之剑。绾曰:“先帝赐臣剑凡六,剑不敢奉诏。”上曰:“剑,人之所施【施:佩戴。】易,独至今乎?”绾曰:“具在。”上使取六剑,剑尚盛,未尝服也。郎官有谴,常蒙其罪,不与他将争;有功,常让他将。上以为廉,忠实无他肠,乃拜绾为河间王太傅。吴楚反,诏绾为将,将河间兵击吴楚有功,拜为中尉。三岁,以军功,孝景前六年中封绾为建陵侯。
其明年,上废太子,诛栗卿之属。上以为绾长者,不忍,乃赐绾告归,而使郅都治捕栗氏。既已,上立胶东王为太子,召绾,拜为太子太傅。久之,迁为御史大夫。五岁,代桃侯舍为丞相,朝奏事如职所奏。然自初官以至丞相,终无可言。天子以为敦厚,可相少主,尊宠之,赏赐甚多。
为丞相三岁,景帝崩,武帝立。建元年中,丞相以景帝疾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,而君不任职,免之。其后绾卒,子信代。坐酎金【酎金:诸侯为天子祭祀上帝宗庙而交给朝廷的贡金。】失侯。
塞侯直不疑者,南阳人也。为郎,事文帝。其同舍有告归,误持同舍郎金去,已而金主觉,妄意【妄意:没有根据地猜测。】不疑,不疑谢有之,买金偿。而告归者来而归金,而前郎亡金者大惭,以此称为长者。文帝称举【称举:提拔。】,稍迁至太中大夫。朝廷见,人或毁曰:“不疑状貌甚美,然独无奈其善盗嫂何也!”不疑闻,曰:“我乃无兄。”然终不自明也。
吴楚反时,不疑以二千石将兵击之。景帝后元年,拜为御史大夫。天子修吴楚时功,乃封不疑为塞侯。武帝建元年中,与丞相绾俱以过免。
不疑学《老子》言。其所临,为官如故,唯恐人知其为吏迹也。不好立名称,称为长者。不疑卒,子相如代。孙望,坐酎金失侯。
郎中令周文者,名仁,其先故任城人也。以医见。景帝为太子时,拜为舍人,积功稍迁,孝文帝时至太中大夫。景帝初即位,拜仁为郎中令。
仁为人阴重不泄【阴重不泄:沉默少语,不轻易泄露他人的事情。】,常衣敝补衣溺袴【袴:同“裤”。】,期为不絜【絜:同“洁”,干净。】清,以是得幸。景帝入卧内,于后宫秘戏,仁常在旁。至景帝崩,仁尚为郎中令,终无所言。上时问人,仁曰:“上自察之。”然亦无所毁。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。家徙阳陵。上所赐甚多,然常让,不敢受也。诸侯群臣赂遗,终无所受。
武帝立,以为先帝臣,重之。仁乃病免,以二千石禄归老,子孙咸至大官矣。
御史大夫张叔者,名欧,安丘侯说之庶子也。孝文时以治刑名言事太子。然欧虽治刑名家,其人长者。景帝时尊重,常为九卿。至武帝元朔四年,韩安国免,诏拜欧为御史大夫。自欧为吏,未尝言案人,专以诚长者处官。官属以为长者,亦不敢大欺。上具狱事,有可却,却之;不可者,不得已,为涕泣面对而封之。其爱人如此。
老病笃,请免。于是天子亦策罢【策罢:下诏书令其辞职。】,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。家于阳陵。子孙咸至大官矣。
太史公曰:仲尼有言曰“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”,其万石、建陵、张叔之谓邪?是以其教不肃而成,不严而治。塞侯微巧【微巧:隐约地投机取巧。】,而周文处谄,君子讥之,为其近于佞也。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!
译文
万石君名叫奋,他的父亲是赵国人,姓石。赵国灭亡以后,石家移居到温县。高祖向东攻打项羽,途经河内,当时石奋才十五岁,当了一名小官吏,侍候高祖。高祖与他谈话,非常喜欢他恭敬的态度,问他:“你家里有什么人?”石奋答道:“我的双亲只有母亲在世,可她不幸双目失明。家里十分贫穷。我还有一个姐姐,会弹琴。”高祖问:“你能够跟随我吗?”他说:“我愿竭尽全力为您效劳。”于是高祖将他姐姐召来并封为美人,任命石奋为中涓,负责管理文书以及大臣谒见之事,还把他家迁到长安城中的戚里,这是由于他姐姐当上美人的缘故。石奋做官做到孝文帝时期,积累功劳官至大中大夫。他虽然不懂经术儒学,但是论起恭敬严谨的态度,没有人能与他相比。
文帝在位的时候,东阳侯张相如担任太子太傅一职,后来被免官。皇上选拔可以接任太子太傅的人,群臣纷纷推举石奋,石奋因此成为太子太傅。等到孝景帝即位时,任命他为九卿;由于他和皇上之间的关系太过亲近,皇上对他有所顾忌,因此调任他为诸侯丞相。石奋的长子石建,二子石甲,三子石乙,四子石庆,都因为性格温顺、孝敬父母、做事严谨而当上了二千石的大官。于是景帝评价道:“石君和他的四个儿子都是二千石的官员,臣子的尊贵荣耀竟然集中在他一家。”由此便称石奋为万石君。
孝景帝晚年,万石君石奋食上大夫的俸禄回家养老,只有在过年和四季更换之时以大臣的身份朝见皇上。在经过皇宫门楼的时候,万石君一定要从车上下来快步前行,看到皇上的车驾,一定要俯下身来扶着车前横木表示敬意。他的子孙当上小官吏,回来拜见他时,万石君一定要穿上朝服接见,而且不称呼他们名字。子孙如果犯了错误,他也不谴责,而是坐在一旁的座位上,对着饭桌不肯吃饭。然后其他子孙便互相责备,最后要通过长辈说情,本人光着上身态度坚决地谢罪,表示一定会改正错误,直到这时他才会饶过他们。已经成年的子孙在他身边,就算平时在家也一定要戴上礼帽,一副整齐肃穆的样子。仆人们也是一派恭敬祥和的气氛,十分恭谨。皇上时常给他家赏赐一些食物,他一定要跪下拜伏在地上吃,仿佛皇上就在他面前一样。他办理丧事的时候,十分悲哀。子孙谨遵他的教诲,为人处事也和他一样。万石君一家凭借孝敬严谨而闻名于各郡各国,即便是齐鲁地区那些品行质朴的儒生,也都认为自己比不上他。
建元二年(前139年),郎中令王臧由于奉行儒学而获罪。皇太后认为,儒学学者言辞浮夸而缺少实质内容,如今万石君一家人说话不多却身体力行,于是就任命他的长子石建为郎中令,任命他的小儿子石庆为内史。
石建年纪大了,头发也白了,而他的父亲万石君却依然健康,什么病也没有。石建担任郎中令的时候,每五天休假一次,回来拜见父亲,总是先进入仆人的小屋,私下里向仆人询问父亲的情况,并拿走父亲的贴身衣裤和便器,亲自洗净,再交给仆人,不敢让万石君知道此事,而且经常这样做。石建担任郎中令,如果有可以议论的事,他背着人畅所欲言,十分恳切;可是一旦到了朝堂上晋见,就好像不擅长说话的样子。因此皇上便亲自对他表示尊敬,并以礼相待。
万石君搬到陵里居住。内史石庆酒醉回家,进入外门的时候没有下车。万石君听说以后,便不吃饭。石庆非常害怕,于是赤裸上身前去请罪,仍然不被接受。全族的人和石庆的哥哥石建都脱掉衣服赤裸上身前去请罪,万石君责备道:“内史是尊贵的人,进入乡里的时候,乡里中的长辈都要急忙回避,而内史则坐在车上我行我素,这本来就是应该的!”于是他便停止追究石庆。石庆与众子弟都进入里门,快步走回到家中。
万石君在元朔五年(前124年)去世。长子郎中令石建痛哭哀悼,必须扶着拐杖才能走路。一年多以后,石建也死了。众子孙都尊崇孝道,而石建最为突出,他甚至超过了万石君。
石建做郎中令时,有一次上书奏报事情,文件批下来以后,石建阅读,说道:“我写错了!‘马’字下面四脚加上马尾应该是五笔,可是现在只写了四笔,缺一笔。皇上发现以后责怪下来我就该死了!”他十分恐惧。石建做事极为谨慎,即便是其他事情也都是如此。
万石君的小儿子石庆担任太仆,有一次为皇上驾车出行,皇上问他驾车的有几匹马,石庆用马鞭挨个数完以后,举起手说:“一共有六匹马。”在石奋的儿子当中,石庆算是最随便的了,然而他还是这样认真。后来他担任齐国丞相,整个齐国的人民都仰慕他的家风,因此不用发布政令齐国便得到很好的治理,于是人们为他修建了石相祠。
元狩元年(前122年),汉武帝设立太子,从群臣中选拔能够给太子当老师的人,石庆因此从沛郡太守调任太子太傅,七年之后升任御史大夫。
元鼎五年(前112年)秋天,丞相赵周犯罪,被免职。皇上发布制书诏告御史说:“先帝十分尊重万石君,他的子孙颇有孝行,因此让御史大夫石庆担任丞相一职,封为牧丘侯。”当时,朝廷正派遣军队向南征讨南越和东越,向东攻打朝鲜,向北驱逐匈奴,向西讨伐大宛,国内事务繁多。天子巡视全国,修复上古时期的神庙,到名山祭祀天地,推行礼乐。国家用度不足,桑弘羊等人便开辟财源为国家谋取钱财,王温舒等人则推行严苛的法律,儿宽等人推崇文才学术官至九卿,他们交替当权,政务不由丞相决定,丞相只是一味地忠厚谨慎罢了。石庆担任丞相九年,在此期间没有发表可以匡正时弊的言论。他曾打算请求惩治皇上的近臣所忠、九卿咸宣的罪行,可是他不但没有让他们服法,反而使自己因此获罪,后来动用金钱才得以赎罪。
元封四年(前107年),关东地区有两百万流民,没有户籍的人数达到四十万,公卿大臣商议此事想请求皇上将这些流民迁到边疆,作为对他们的处罚。皇上认为,丞相石庆年老谨慎,是不可能参加这种讨论的,于是便赐丞相回家休假,然后就追查御史大夫以下议论并奏请此事的人。丞相因为自己不能胜任而感到惭愧,于是上书说:“我有幸担任丞相,但是我愚钝无能,不能辅助天子治理国家,致使城郊仓库空虚,许多百姓都流离失所,我有这样的罪过,按律应当被杀,可是皇上不忍惩治我。我愿意归还丞相和侯爵的印信,乞求让我告老还乡,给贤能的人才让路。”皇上说:“现在粮仓已经空了,百姓贫苦不堪,流离失所,而你想请求我下令迁移他们,现在国家已经动荡不安了,动荡就会带来危机,而你现在想要辞去相位,你打算要把这危难推给谁呢?”皇上用诏书责备石庆,石庆羞愧难当,于是重新处理政事。
石庆心思细密、处事小心谨慎,但是没有什么别的大谋略,也没有替平民百姓说过什么话。此后过了三年多,在太初二年(前103年),丞相石庆去世,谥号为恬侯。石庆的二儿子石德,石庆生前非常喜爱、器重他,皇上就让石德继承石庆的侯爵之位。后来石德当上了太常,因为犯法理应处死,以金钱赎罪免除死刑,降为平民。当初石庆担任丞相的时候,他的子孙做官陆续做到二千石级别的有十三人。等到石庆去世以后,他们逐渐因为犯罪而被免职,孝敬、谨慎的家风也更加衰败了。
建陵侯卫绾,是代郡大陵人。卫绾起初凭借高超的车技而当上了郎官,侍奉汉文帝,由于连续立功而获得升迁,当上了中郎将,他除了忠厚谨慎之外没有其他才能。孝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,有一次把皇上身边的人召来饮酒,而卫绾以生病为由没有来。文帝临终之际,嘱咐景帝说:“卫绾品行端正,你以后要好好对待他。”等到文帝去世,景帝即位,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没有责备卫绾,卫绾则一天比一天谨慎勤勉。
有一次景帝去上林苑,命令中郎将卫绾陪同乘车,回来时景帝问道:“你知道你为什么能与我同乘一辆车吗?”卫绾说:“我从一名车兵有幸能够凭借连续立功而升至中郎将,不知道为什么。”景帝问道:“我过去做太子的时候召你来,而你却不肯来,这是为什么?”卫绾答道:“微臣死罪,我当时的确生病了!”皇上赐给他一柄宝剑。卫绾说:“先帝在世时曾赐给我六把宝剑,我实在不敢再奉诏命接受陛下赐给我的剑了。”皇上说:“剑,是人们的喜欢之物,可以用来佩戴交易,难道那些剑一直留到现在吗?”卫绾说:“那些剑都在。”皇上就让他取来那六柄宝剑,宝剑还插在剑鞘中,从来没有使用过。郎官如果有过错,卫绾常常替人承担罪责,而不与其他中郎将争执;有了功劳,他也常常让给别人。皇上认为他廉洁端正,忠厚而没有杂念,于是任命他为河间王太傅。吴楚反叛之时,皇上任命卫绾为将军,他统领河间的军队攻打吴楚叛军有功,因而被任命为中尉。三年以后,卫绾立下军功,在孝景帝前元六年(前151年)被封为建陵侯。
第二年,皇上废掉太子刘荣,又杀死太子的舅父等人。皇上觉得卫绾忠厚,不忍心惩罚他,就让他休假回家,而派郅都逮捕并惩治栗家的人。事情办完以后,皇上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,并征召卫绾,让他担任太子太傅。过了很久,卫绾升任御史大夫。五年以后,他接替桃侯刘舍担任丞相,在朝堂上奏请事情只是按照职责归属来办事。然而他从一开始做官一直到当上丞相,始终没有什么建树。天子认为他为人敦厚,可以辅佐少主,因此十分尊重和宠信他,给他的赏赐也很多。
卫绾担任丞相三年以后,景帝去世,武帝即位。在建元年间,由于当初景帝患病时各官署的囚犯有很多都是无辜受罪的,丞相因此被认为不称职,最后被罢官。后来卫绾去世,他的儿子卫信继承了爵位。后来,卫信由于助祭献金不符合规定而失去了侯爵之位。
塞侯直不疑,是南阳人。他做郎官,侍奉汉文帝。他的室友请假回家,误拿走了同房郎官的黄金,不久黄金的主人发现,就没有根据地猜测是直不疑偷了自己的黄金,直不疑道了歉,承认是自己所为,于是买来黄金偿还他。那个请假回家的人回来以后归还了黄金,这时先前丢失黄金的那位郎官十分惭愧,因此称赞直不疑是一个忠厚的人。文帝提拔人才,直不疑逐渐升至太中大夫。有一次上朝拜见皇上,有人诽谤他说:“直不疑外表很美,可是唯独没有办法处置他喜欢和嫂子私通的事!”直不疑听了以后说道:“我根本就没有哥哥。”说完以后最终也不再为自己辩白。
吴楚七国反叛朝廷的时候,直不疑以二千石官员的身份率领军队前去攻打叛军。景帝后元元年(前143年),他被任命为御史大夫。皇上奖赏平定吴楚之乱的功臣,就封直不疑为塞侯。汉武帝建元年间,他与丞相卫绾都因为过失而被免职。
直不疑学习《老子》的思想。他到每个地方做官,一切都按照旧章程处理,唯恐别人知道他做官的事迹。他不喜欢为自己树立名声,被人们称为有德行的人。直不疑去世以后,他的儿子直相如继承了爵位。到了他的孙子直望继承祖业的时候,由于助祭献金不符合规定而失去了侯爵。
郎中令周文,名叫仁,他的祖先原本是任城人。周仁凭借医术进见皇上。当初景帝做太子时,任命他做舍人,后来由于积累功劳而逐渐升迁,在孝文帝时期当上了太中大夫。景帝刚刚即位,就任命他为郎中令。
周仁为人沉默少语而不轻易泄露他人的事情,经常穿着缀有补丁的旧衣服和能够吸附尿液的内裤,还经常故意使自己不干净,使嫔妃不愿接近从而得到了景帝的宠信。景帝进入寝宫,和后宫的嫔妃暗地里嬉戏,周仁常在一旁。等到景帝去世,周仁还是担任郎中令,始终没有发表具有建设性的言论。皇上经常向他询问别人的情况,周仁总是回答:“还是皇上自己去考察他吧。”不过,他也没有诋毁过别人。正是因为如此,景帝曾两次亲自到他家里。周仁的家迁到了阳陵。皇上赏给他很多财物,可是他经常推辞,不敢接受。至于诸侯和百官给他的贿赂和馈赠,他始终都没有接受过。
武帝即位以后,认为周仁是先帝时期的老臣,因而非常尊重他。于是周仁便因病免职,以二千石的俸禄告老回家,他的子孙全都当上了大官。
御史大夫张叔,名叫欧,是安丘侯张说的庶子。孝文帝在位时他凭借研究法家的刑名之学而侍奉太子。虽然张欧喜欢研究刑名之学,但他为人忠厚。景帝在位时,对他十分尊重,他因此常常位列九卿。到了武帝元朔四年(前125年),韩安国被免去官职,皇上下诏任命张欧为御史大夫。张欧自从步入仕途开始,从来不说惩治有错之人,而是一心一意地用诚实忠厚的态度做官。他的属下认为他是一个忠厚的人,也不敢过分欺骗他。皇上将需要审理的案子交给他,有的可以退回重审,就把它退回;如果不能退还,是因为不得已,他就流着眼泪亲自看着把文书封好。他爱护别人的情形如此。
张欧年老而病重,因此请求免职。于是天子特别颁布诏令,准许他离职,并按照上大夫的俸禄让他回家养老。张欧的家安置在阳陵。他的子孙都当上了大官。
太史公说:孔子曾经说“君子说话要谨慎而行动要积极”,这说的大概就是万石君、建陵侯、张叔等人吧?所以他们做事并不峻急却能成功,方法并不苛刻却能使社会安定。塞侯直不疑隐约地投机取巧,而周文则陷于阿谀,君子之所以讥笑他们,是因为他们接近于奸巧谄媚。但他们也称得上是行为敦厚的君子了!